
《我不是药神》虽然在形象塑造、细节处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但是因为触及社会的痛点、带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少有的现实主义力作。同时,它也塑造了一个平民英雄,一个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的济世英雄,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影中少有的正面形象,因此而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通过该片也可以看出,电影不仅仅是娱乐的艺术,更是载道的艺术。

《我不是药神》建构了一个不让观众出戏的银幕世界,通过戏的魅力让那些看似世俗的相貌在银幕现实中具有了崇高的美感和道德力量。《我不是药神》是一部有着极强指示意义的作品。它揭示了在新时代的今天,民生诉求和国家精神如何在银幕世界中得到呈现。

19世纪末,欧洲艺术在摄影出现之后,试图脱离写实主义。浮世绘的流行改变了欧洲画家对绘画的认识,开启了20世纪艺术史中现代主义与东方主义这一最为重要的议题。西方绘画线条中的自性表现出现在20世纪初,抽象表现主义的线条和笔触借鉴了中国的书法形式。现代主义和东方主义真正开始在绘画性上转向一种语言间性,即书法性与抽象主义的对话。现代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对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样发生在激浪派的偶发艺术,试图将观念艺术发展为一种禅宗化的后观念主义。战后前卫希望重建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后观念主义是现代主义对东方哲学的随机性和日常意义的认识论的吸收。最后,亚洲战后艺术对后观念主义重新定义,日本具体派和物派,韩国的单色画,在参照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在观念退出的领域,借助东方哲学进行

本文将现代主义戏剧置于20世纪戏剧史的发展脉络之中、置于欧洲哲学理性 非理性的转型过程之中,讨论其如何在与现实主义的对话关系中,在欧洲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成不同艺术风格与理论流派。在这样的辨析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现代主义的不同流派,往往是和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不同问题相关。本文希望通过梳理欧洲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脉络,还原现代主义戏剧的不同场景,为中国戏剧如何以自己的民族传统为基础,在与各种不同的外来思潮碰撞过程中,建构自身的戏剧理论语言做一定的学术积累。


优秀的文艺作品创造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艺术形象,不仅给人以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启迪和对情感道德的净化提升,而且还给人提供健康向上的审美娱乐。

当前草根文学评论主要形成了“剜烂苹果”式、“站在低处说话”式和“跟踪引导”式三种评论,已经拥有一些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文学评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对中国文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就艺术研究来说,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交汇、冲突、过渡中,分析和总结网络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新实践与新美学,不仅具有个案上的典型意义,还具有文艺美学乃至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上的普适价值。

只有基于对真理无条件的服从,以及对自己视为志业的评论事业的神圣信仰,才能使批评避免寄生的冗余,真正成为艺术强有力的护法。而要做到这一点,评论家能否知所敬畏、常怀诚意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当代油画的自塑过程是一个自我更新与重造的过程,也是20世纪以来油画民族化与本土化观念的延续与提升,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偶然性,其旨归仍是油画的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更应自觉加强人格修养和艺术修为,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守正律己、遵纪守法,坚决抵制涉黄涉毒、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真正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把德艺双馨作为毕生的追求。

近年网络剧发展迅速,尤具特色的当属悬疑、推理、罪案题材。罪案剧是网络时代文化语境中的新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罪案剧主人公的精神气质则更接近于“游侠”,“疏离”是其话语策略;价值取向方面,罪案剧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体现出批判性,罪案成为社会隐喻。从某种意义上看,罪案剧拥有了当下影视作品少见的现实主义品格。对于包括罪案剧在内的网络文艺来说,现实主义是对社会文化状况的深刻体察,是审美主体的真实表达,是一种主动性的、交互性的审美实践。

现实题材是当下戏曲创作不可回避的选题主要来源,不少作品却因其照搬生活、缺乏戏剧性而被诟病。一些现实生活中感人至深的真实事件和人物被搬上舞台后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方面需要创作者注意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差异,同时,更要尊重戏曲创作规律,并积极向传统借鉴学习,丰富现实题材戏曲创作的手段和表现力。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为统领,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锐意进取,为繁荣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新的贡献。

“新时代”是一个大时代,电视剧创作的“富矿”深蕴其中。电视剧只有充分挖掘其中丰富的生活、鲜活的人物、时代的精神进入创作视域,才能为“新时代”留下发展的注脚,为后代留下时代的记忆,电视剧也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责任与时代担当。其中,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任重道远。繁荣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要理性而为,就要充分考量社会心理、时代精神、艺术创新等因素,切实推进电视剧的题材拓展、形象塑造、情节创新、现实主义精神注入等,从而实现多点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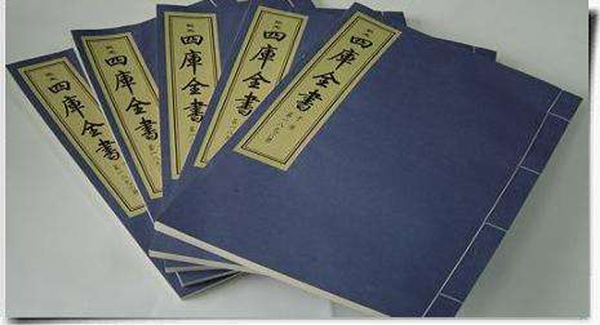
“形式”概念是舶来品。《新尔雅》将该词作加点处理,指明它是日源词,但从本源看实属“旧词新义”。它在古汉语文献中一度出现,其基本词义即至今天也仍在使用。王国维、梁启超等赋予了新的特点,主要体现是与“内容”“实质”等构成一对范畴而逐渐泛用开来。与“精神”构成一对范畴,且带有明显的诉求革命的功利色彩,这成为在后来使用中最明显的变化。“形式”的源流情况,大体反映了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相媾和的历史情境,亦突显出当今展开中西关键词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

对“美情”的追求和倡扬,是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神髓之一。“美情”要求对日常情感进行审美升华,重视美的情感与真善之贯通,由此可以对当代艺术理论批评的种种非美趋向予以观照反思。“美情”的命题,也要求理论家批评家提升情感能力,重视情感品格,尤其是传承弘扬中华美学以真善美贯通为要旨的大美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