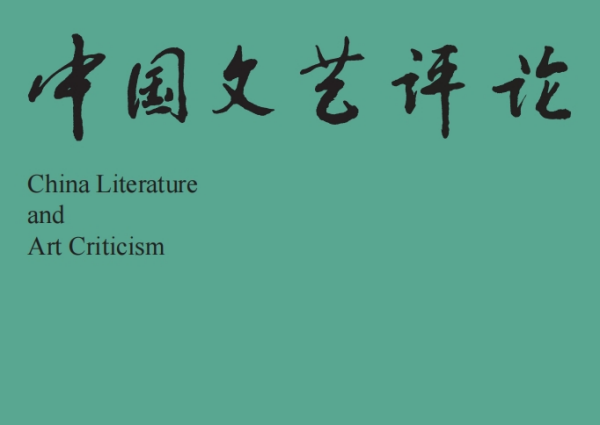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要“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在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引下,文艺界涌现了一大批展现新时代崇高之美的精品力作,广受人民群众喜爱和好评,但同时存在着调侃崇高、扭曲经典,脱离人民群众等问题。为此,本刊以“崇高之美的时代表达”为题,约请专家学者从新时代文艺在美学层面上的崇高表达这一角度切入,结合代表性文艺作品,挖掘并阐述新时代崇高美的样式与特征,彰显新时代文艺对崇高之美的追求与张扬。
新时代国产电视剧的崇高美学表达
【内容摘要】 新时代以来,在党的政策方针指引下,文艺领域涌现了一系列以崇高精神为表现主旨的电视剧。其中既有着眼于革命历史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又有描绘平凡大众或时代功勋的现实镜像。这些电视剧的主题内容与形式表达高度契合,不仅挖掘视听语言的崇高表意功能,也以悲剧性书写的方式激发观众内心的崇高感受。当下电视剧市场存在过度追求热度与噱头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对崇高创作进行再度讨论,崇高美学的表达完成了对观众主体的询唤,更抚平了现代性异化的裂隙,唤醒人民的崇高心灵。
【关 键 词】 崇高美学 国产电视剧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人民性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作为一种悠久且贯穿人类文明发展的超越性精神,崇高再度成为了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对象。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电视剧创作中也不乏崇高精神的展现,不论是《觉醒年代》《问苍茫》等扎根于革命历史的深情回望,或是《功勋》《大山的女儿》等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深刻记述,抑或是《大江大河》《山海情》等着眼于平凡大众的生活书写,崇高精神皆以跨越时空的方式呼唤且触动着大众。
一、新时代电视剧创作的崇高书写
作为一种精神指引,崇高一直是国产电视剧所传递的重要特质之一。正如崇高在哲学上的多义,崇高在电视剧创作中也有多样的展现,既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历史伟人的家国情怀与悲剧表达,也有时代先驱上下求索的人类超越性的展现。
(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崇高显现
朗吉努斯在以古希腊艺术作品为文本对崇高进行的最初论述中指出:“崇高是高尚心灵的回声。”不同历史时代、国家地区的文艺创作都有其所注重的崇高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影响与文化强国建设的指引下,我国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成为了承载崇高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崇高是革命精神跨越时空的视觉性复写;另一方面,在生动的表达中,观众得以重回历史现场,在艺术感化中实现崇高感的接受。崇高作为“伟大的思想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定义,在生命的局限中寻找超越”之意,成为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精神内核,革命伟人也随即成为了此类电视剧创作较为青睐的崇高主体之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崇高书写,主要体现在对革命伟人精神的深沉表达中——于时代困局中坚毅不屈的革命信仰、求新求变的超越精神、涵养深沉的家国情怀,等等,皆是历史性的崇高显现。
新时代以来,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的背景下,愈来愈多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争相涌现:《觉醒年代》让观众看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革命艰辛,《问苍茫》在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书写中实现伟人形象的聚焦和历史群像的平衡。两部剧作前后贯通,从时间线上完整复现了1915年到1927年这段在影视剧创作中稍显空白的历史时期。虽然题材内容与叙事角度另辟蹊径,但上述两部剧作在创作时仍旧瞄准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基点——历史伟人在社会转向过程中涌现的家国情怀——这也正是此类型电视剧表达崇高精神的主要方式。正如“家国情怀”对家与国的各自着重,在《觉醒年代》中观众既可在重回历史现场时看到革命志士为民生嗟叹,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的琐碎表达中感受其崇高的精神品格。例如李大钊在走出校园的田野考察中,看到与公鸡拜堂的少女,深深为国人的封建陋习而感到痛心,亦深感中国的革命路径需要实现从精神性向国民性的转变。在生活细节的塑造中,该剧也着重刻画了李大钊慷慨解囊的善良性格,比如典当值钱物件为工人葛树贵的小孩治病提供经济支持,为了补助贫困学生而无法兑现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承诺,等等。
康德认为:“在道德品质上,唯有真正的德行才是崇高的”,《觉醒年代》即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共同着手实现对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崇高德行塑造。“崇高的情感本质上是崇敬感”,崇敬感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崇拜。这种情感来源于不同人格人群为人处世的相异,来自于伟人对于普通人的超越,同时也来自于影像塑造中伟人不凡特质的展现。不论是宏观的忧国忧民,或是微观的慷慨相助,历史和生活细节两个向度皆展现出李大钊的超人性格与超凡品质。这不仅激发了观众内心的崇敬之感,也实现了人物崇高性的表达与塑造。
生活书写与历史现场的结合也是当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塑造人物的方式之一。在电视剧《问苍茫》中,历史记载中寥寥数笔的蒋先云成为了观众铭记的对象。事实上,正是历史文献中的“寥寥数笔”,给予了该剧充分的创作空间。比如,历史上的蒋先云在黄埔军校第一期表现优异,并在军校毕业后留任为蒋介石秘书,在剧中是以“步石随云起,题诗向水流”等细节具象化蒋介石对于蒋先云的欣赏。在对蒋先云牺牲的刻画中,剧集也给予了历史事件与个体情感的双向铺垫。一方面,蒋先云陷入国民党的党内猜忌;另一方面,发妻的离世也给予他精神沉重一击。于此,剧集创作努力以生活化书写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首先明确其亦为怀有爱恨情仇的普通人,再以历史事件中的拼搏、奉献、牺牲精神阐释其超越性与崇高性。
崇高是令人敬重的精神品格,但它不是历史伟人的特例。它是不凡的,同时也是平凡的。系列电视剧《理想照耀中国》中“守护”一集,选取了革命烈士张人亚之父张爵谦受儿子所托,几十年如一日守护国家机密档案的故事。作为一介农夫,平凡的他虽看到了社会的动荡,却也只是被历史的洪流推赶向前,他无法预知“大家”的未来,却在“小家”中谨记儿子的嘱托。张爵谦在革命历史中所体现的崇高不是主动选择的,而是被动形成的,但就在这被动的过程中,他目击了诸多爱国青年的前仆后继,也愈加理解儿子选择的革命信仰。不同于历史伟人、超人的能力与坚定的信仰,张爵谦的动人之处在于他真正贴近了绝大多数的受众——他们或许没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能力,却在平凡人生的无常中渐渐体悟信仰的真相。
(二)时代发展的崇高镜像
崇高的发展也有其历史变化,从朗吉努斯“高尚心灵的回声”到伯克“某种令人欣喜的恐惧,某种带着害怕的平静”,崇高的内涵实现了由超越性向痛感的变化。发展至康德,崇高的意涵再度实现飞跃,他沿用伯克“痛感”的观点,但为其注入了更多积极的内容,将激发人类内心情感的崇高分为“恐怖的崇高”“高尚的崇高”和“华丽的崇高”。然而,这种以感官为基础的崇高很快也为康德所更新,“我们‘被扔出了自我感官的局限’并且抓住了‘自己内心的理性的崇高性’,达到认知的自由,克服了自己的局限性,摆脱了对属于经验世界的那一部分自我的依赖,实现了精神的自治”。“克服自己的局限性”与朗吉努斯“在生命的局限中寻找超越”形成跨越时空的互文。二者都强调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性,但在康德这里,他已然更为强调人类对于自然限制的宰制与征服。
当然,人类也是在对客体的征服过程中,体现其自身的能动性与超越性的。这种对于自然的征服与超越,在电视剧《山海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作为一部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时代献礼剧,《山海情》讲述了偏僻荒芜的西海固在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努力下,由“干沙滩”变为“金沙滩”的故事。《山海情》将视点转向生活中真正的普通人,以人民史观的视角呈现人类面对自然时不屈不挠的品质与人定胜天的信念,由此实现崇高精神的价值传递。《最美的青春》中同样如此,为解决恶劣自然环境对于生存与发展的困囿,年轻的村干部带领村民一同将青春与汗水挥洒在祖国的戈壁滩中,书写下时代的壮丽篇章。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不仅未回避现实中的挑战与难题,而且深刻地将人物刻画得真实可感,还原了人性本真的光辉。剧中的普通民众或许并未怀揣深刻的政治觉悟,他们的心思更多地聚焦于眼前的生计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然而,正是这亿万平凡个体的汇聚,共同铸就了国家的蓬勃发展。事实上,直指“人类超越性”的崇高是最具公平性的名词,它如同善恶等品质般,不问阶层出身而先天性地灌注在人类的生命中,只待一个契机将其发现。

在与自然的抗争之外,与顽固封建思想的对抗也是人类能动性与超越性的体现。《功勋》中《申纪兰的提案》篇章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为复现对象,讲述了在“好男走到县,好女不出院”的封建时代中,申纪兰如何带领女性寻求与男性平等地位、追求自由解放的故事。申纪兰不仅成立纺花组,让女性加入可以获得物质报酬的社会劳动,还成立妇女互助会,带领女性下地干活,冲破千百年来封建陈规的桎梏,更在农村合作社的时代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思想,使对于妇女劳动的重视于全国普及开来。《山花烂漫时》则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事迹为蓝本,多维视角描绘新时代女性成长与抗争的壮丽画卷。剧中,张桂梅以非凡的毅力与决心,致力于改写贫困山区女性的命运轨迹,展现了无尽的奉献与坚持。同时,魏庭云等女教师群体在教育一线默默坚守,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追求着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此外,以谷雨为代表的一群山村女学生,怀揣梦想,奋发图强,誓要走出大山,拥抱更广阔的天地。正是在与封建思想的激烈交锋中,人物的深刻内涵与独特魅力得以熠熠生辉,并展现出耀眼的弧光。
脱贫攻坚和疫情防控是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缩影。正如伯克在分析崇高时所言,“崇高所涉及的自我保存原则是关乎生存的欲望”。《大山的女儿》《在一起》等电视剧就是在现实镜像中发现人们的崇高品格。在电视剧《在一起》中,一方面,疫情的肆虐激发了人们追求自我保存的欲望,引起了大众灵魂的震颤与生命的挣扎,从而抵达了饱含痛苦的某一切面的崇高。另一方面,在医生这一群体上,崇高达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们为患者尽心竭力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生存可能——人类原始的欲望被覆盖、被超越,以一种具有炙热信仰与无私奉献的“距离感”抵达了常人所不能触及的高度。而在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中,黄文秀时刻心系百坭村的百姓,这份牵挂使她在风雨之夜前脚与父母告别,后脚就踏上了回村的归途。但这次道别却成了永别,黄文秀在日夜的操劳中忘却了自我。正如其宣传语中所说:“有些人从山里走了,就不再回来,你从城里回来,却再没有离开。”在崇高理想的感召之下,个体实现了对浅薄欲望的舍弃与超越,从而展现出非凡的力量与崇高的品格,进而唤起群体性的精神共鸣。
二、新时代国产电视剧崇高美学的塑造方式
相较于其他叙事艺术而言,电视剧因其作为视听艺术所具有的直观性特质而使其在叙事发生之前,便可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呈现率先触动观众的心灵。基于此,新时代以来的国产电视剧创作一方面巧妙运用了一系列饱含崇高情感的视听元素,以强化其精神内涵的表达与呈现,另一方面,通过对于细节设计的精雕细琢,建构历史在场的悲剧性书写,使得观众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悲壮。
(一)崇高美学的视听呈现
文字表达与情节叙述是崇高精神传达的渠道之一。同时以电视剧的视听特质为基础,崇高也以一种视觉性的方式得以呈现。事实上,在哲学家讨论崇高的意涵之初,就将视觉性纳为评判要素之一。“崇高的事物在尺寸上是巨大的,而美的事物则是娇小的……崇高的事物则是粗糙不平的……崇高的事物在很多情况下却以直线条的方式出现,即便存在偏离也是极为明显的……崇高则倾向于黑暗和晦涩……崇高则坚固甚至厚重。”在伯克关于崇高的形式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窥见哲人对于崇高感的既定印象。尤其将其与优美进行对比时,崇高更为凸显其雄伟庞大的特质,以及此种呈现作用于人们视觉时激发的压倒性的心灵感触。张艺谋在《黄土地》的摄影分析中言及:“在画面中,坚决排斥可有可无之物,强调简炼、强调大块面的厚重感”,这里大块面的厚重感即在视觉呈现上形塑了黄土高原辽远庞大的崇高感。
电视剧与电影虽同为视听艺术,但从播放媒介和受众群体出发,电视剧的视觉艺术呈现显然更具大众性。因此,即使在同样以黄土高原为背景的《山海情》中,我们虽会见到黄土漫天与飞沙走石,却不会看到土地大面积挤占天空的情形。但即便受限于媒介性质,电视剧在创作的过程中仍会选择具有崇高意涵的视听语言,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契合。在电视剧《问苍茫》中,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黄埔军校开始清除共产党的一场戏中,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会议上让共产党员选择退出共产党(图1-1),此时镜头落到人群中蒋先云的脸上,只见他眉头紧锁、面色凝重(图1-2),片刻过后,他利落地举起右手,此时的镜头顺应他举手的动作,从他的面庞自然地移至他高举的右拳(图1-3、1-4)。宣讲台上的蒋介石和台下的同伴稍显错愕,镜头很快又回到了蒋先云凝重的面容上(图1-5)。在这里,无论是给予蒋先云镜头中心的位置,或是对其紧攥的右拳和凝重的面容予以特写,皆与蒋先云坚定的革命信仰完美契合,从形式和内容上共同实现人物崇高信仰的塑造。不止于此,在蒋先云发表其退出国民党的声明时,摄影机以仰角的形式对其进行拍摄(图1-6),从视觉出发凸显其思想之崇高。与此同时,镜头围绕其身体缓慢移动,蒋先云身后闪烁的阳光愈加炽烈,直至其背后的光辉完全露出(图1-7),实现其崇高精神的外化。

电视剧《问苍茫》中运用视听手段实现的崇高精神表达
视听语言作为影视艺术独特的语法,在影视创作中具有独特的表意作用,特写和仰拍即是其表达崇高感的主要方式。这种视觉表达方式不仅如伯克所述,“崇高的事物在尺寸上是巨大的”,也是“保留了康德意义上的物的崇高感,即体积、形态、质量的无比庞大”。尤其在崇高客体和非崇高客体的对比之中,视觉修辞更为凸显崇高物象的压倒性特质,强化崇高精神的表达。
崇高不仅是视觉上庞大的量感,也是一种氛围感的塑造与烘托。电视剧《觉醒年代》有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蒙太奇段落——青年毛泽东出场的场面。在这组场景中,青年毛泽东怀抱书籍,在雨中穿越人群,旧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跋扈的军官、乞讨的穷人尽收眼底……旧中国百姓水深火热的景况就被浓缩在这短短的108秒之中。在这里,崇高意象的传递不仅是社会背景的宏大,更是青年毛泽东深受触动后沉积的救国救民之志。倾盆的雨是彼时满目疮痍之中国的摹写,而青年毛泽东怀抱书籍、未擎雨伞、逆向而行,则是他坚毅人格和伟人形象的生活化呈现。这一精心排布的段落辅以激烈悲怆的音乐,从视觉的广度与深度上深深震颤着观众的内心。
“崇高风格的另一个源泉就是我们准确无误地找到最适当的本质成分,把它们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此,电视剧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在选定其表达的中心对象后,视觉、听觉及叙事的平衡便是重中之重。《山花烂漫时》中,于华坪女子高中首届高三学子高考落幕之际,张桂梅校长孤身步入夜色中的空荡教室,抒情旋律伴随着冷色调画面的铺展,悄然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孤寂氛围。然而,正当张桂梅校长即将转身离开之时,一曲由毕业学生演绎的《让世界充满爱》响起。导演以过肩镜头的形式将声源交代,只见学生们手中的烛光汇聚成璀璨的光芒,瞬间将周围的冷色调转化为温馨而充满希望的暖色调。叙事、画面和声音的突转与平衡,以震颤观众心灵的方式实现崇高感的传递,进而实现爱森斯坦口中“1+1>2”的效果。
(二)崇高美学的悲剧性书写
或彪炳千秋,或籍籍无名,历史的进步、革命的发展离不开革命者的前仆后继,而时代的险阻、异党的阻碍等因素,皆成为了革命道路上的困难与挑战。克服与超越不仅是彼时的时代命题,也成为了电视剧情节建构曲折性的来源。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延年与陈乔年牺牲的片段令观众印象深刻。上一秒,两人还是与父亲道别、志在远方的进步青年。下一秒,在画面的叠化中,精致的皮鞋已变作戴着镣铐的赤足,平坦的路途布满沙石鲜血——1927年与1928年,陈延年与陈乔年先后被国民党杀害,时年29岁与26岁。在这一段落的悲剧书写中,编导以蒙太奇融合了两个时空,强化希望与绝望的对比。然而无论是前往法国学习,还是奔赴刑场,兄弟二人的眼中都闪烁着灼热的光辉与坚定的希望——因为无论是哪一条道路,他们都在力所能及地为旧中国寻找生之希望。正如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延年所言:“我现在决心要为了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幸福而牺牲一切,我做不到像有些人那样两头兼顾,所以我只能牺牲自己,义无反顾。”青年是国家的希望,青年时期在个人发展阶段中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与希望,陈氏兄弟等更多风华正茂的革命先烈却用他们的生命交换中国的未来,用他们的青春换取中国的成长,这种个体人生的悲剧与整体国家之希望的对比同样强化了信仰坚定的崇高精神。

英勇牺牲是革命者对党和祖国的奉献,而在宏大叙事之外,平凡生活中也常有闪烁崇高精神的不凡时刻。年代剧《大江大河》中,宋家姐弟在恢复高考后如愿考入大学,但在资料提交阶段却因为家庭成分频频受阻,与政府部门一番交涉后,二人只获得了一个上学名额——姐姐宋运萍虽心有不甘,却仍是含泪写下了自愿放弃的决定书,让弟弟宋运辉获得上学的机会。抛开性别视角,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付出与奉献,闪烁着的是不亚于宏大叙事的崇高光芒——因为其已奉献出了其所能付出的所有(当下、也是未来发展的可能)。这是宋运萍个人的悲剧时刻,所以她落下眼泪,但这也是她力所能及地实现亲人梦想的时刻,所以她亦无怨无悔。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作出定义,认为悲剧“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至于怜悯,特里西诺指出:“怜悯是为了某种不幸或似乎不幸的事而发愁,这种不幸可能是致命的或痛苦的,而且落于不应受难的人身上,于是旁观者想到自己或他的亲友也可能遭到这种不幸。”于是,怜悯这一情感的产生实际上隐性地划分了人群——怜悯者/旁观者与被怜悯的对象/经历者。两者之间相隔的不仅是事件的可能性,而且暗含着心理的距离。在《觉醒年代》或《问苍茫》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观众早已远离那一动荡飘摇的岁月,并且已经知晓革命先烈的结局,所以他们内心的怜悯更多地被先烈的超越性所压倒——他们理解并已接受先烈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于此,电视剧选择加入情感化或生活化的内容,在儿女情长的点缀与家国同构的书写中强化先烈高洁坚毅的革命意志,同时让观众重新理解先烈在成为先烈之前,也是有血有肉的平凡大众。比如为陈延年加入柳眉这一情感角色,或刻画蒋先云与其妻的生活细节。在《山海情》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李水花这一角色也更为贴近大众。命运多舛的她因经济受限无法受到教育,后被父亲换了一头驴、两只羊、两笼鸡的彩礼,然婚后不久,丈夫又因意外半身瘫痪……悲惨的命运笼罩着她,其中的失意与无常又是多少普通人的生活常态。然而这一角色的魅力正在于她乐观坚毅的人格,她激发了观众的怜悯,却又打破了观众的怜悯,以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向命运抗争的超越性激发观众的崇敬之情。
无论是怜悯或是恐惧,其中所包含的心理距离都是观众业已知晓这一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当危险直接作用于我们时,它们只会带来真实的痛苦,可是如果我们是旁观者,目睹危险,却不用体验危险,恐惧引发的痛苦感就会转化为幸存的庆幸感,形成‘某种令人欣喜的恐惧,某种带着害怕的平静’,那就是崇高快感的由来。”于此,悲剧美学所激发的崇高感受实际上是作用于“间离性”的心理之上的。崇高比怜悯更为复杂的部分在于,怜悯情感出现后,人们会作出行为选择——避之不及与迎难而上导向的是相反的两极——潜藏于人们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就此得到激发: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平凡或伟大,人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崇高的可能。
三、人民文艺与崇高美学的关联
文艺作为现实生活的艺术化书写,其本质决定了它必须紧密贴近人民群众,以人民为导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这种“人民性”的文艺创作导向更加凸显其重要性。电视剧作为颇具影响力的大众艺术形式之一,其对于崇高美学的追求与展现,更是对文艺“人民性”属性的生动诠释。新时代电视剧的崇高美学展现不仅体现为以人民为导向,也彰显了独特的共时性特质。
(一)影视艺术创作的人民性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化书写,是一个时代的风貌展现,也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指引。文艺的性质指导文艺的创作,同时也引导着观众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提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其后,列宁也再次强调了文艺与人民性的关联,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社会主义文艺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人民为创作与接受对象,来源于人民,反哺于人民。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人民性”的关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深入理解上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文艺创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文艺的“人民性”属性一直是我国文艺创作的重要指引,文艺要以人民大众为基准、以人民大众为导向,生产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这一点上,较早于电视剧诞生的电影艺术有着更为丰富的实践范例。“十七年”时期(1949年—1966年),“广大电影工作者紧贴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确立了‘人民电影’的服务对象、叙事构架、历史视野和美学范式,更加突出电影艺术的‘人民性’”,留下了一系列记录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情感的佳作。20世纪8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的电影故事片开始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但随着“主旋律”类型化与程式化弊病的暴露,加之电影产业的升级,讲述中国故事的重任已落到了“新主流电影”的身上。近年来,传递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新主流电影不仅成为时代发展的镜像,更在票房口碑的节节攀升中成为观众青睐的对象。
与电影艺术相比,电视剧艺术更具大众性,更具备讲述故事的优势,其庞大的体量有利于故事的全面展开。比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可以更为细致地刻画所涉及的革命群体,让更多不为人熟知的历史得以被看见;年代剧、重大现实题材剧则摹写着时代的多元群像,让观众感受到坚定的精神信念和生活的多种可能。此外,电视剧是“陪伴型”艺术,它是人们日常工作后触手可及的休闲娱乐。这种“陪伴”其实也与其传播渠道与播放媒介有着深度关联,它决定着电视剧在创作之初就必须以受众为旨归,必须讲述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一经典论断早已指出艺术是筛选、加工过后的艺术化生活。因此,当一些低俗乃至媚俗的电视剧创作充斥银幕之时,当创作出现只追逐市场热度与噱头的不良倾向时,当电视剧在市场乱象中渐渐偏离艺术的轨道时,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电视剧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崇高主旨。
(二)新时代电视剧崇高美学的生成机制
如前所述,在当下电视剧创作中焕发生机的崇高美学,一定程度上是市场乱象中电视剧艺术再度担负起指引人民的责任的需要。但为什么是崇高美学?复现历史或记录时代的崇高与大众又有怎样的关联?从崇高的定义出发,回到朗吉努斯最早的讨论,“我们的肉身固然受限,人的生存目的却不是为了肉身的存续,而是为了精神升腾……崇高意味着伟大的思想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定义,在生命的局限中寻找超越”。于此,崇高是一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人类共同的崇拜与追求,它在人类对于自身力量的认同中最终抵达对于伟大自身的肯定。
因此,当观众于电视荧幕前观看传递崇高美学精神的电视剧时,其实际所经历的是“对角色的肯定——对自我的认同”这一过程。
首先,电视剧的受众在观赏电视剧内容时,会将自己放置在观赏者的位置上——这或可被理解为崇高美学共时性生成的心理机制——与情节和人物产生的心理距离是怜悯及恐惧产生的前提,也是崇高感产生的基础。其次,由于“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观众即站在了“旁观”与“经历”的交叉点上,他们同情着剧中人物的遭遇,同时,剧中人物的遭遇也是大众所经历的不幸的变体——不幸事件背后所流露的迷茫、困惑、挣扎、悲伤,是人类生命经历的共性,而崇高背后的超越性是人类旺盛生命力的凝结。因此,观众虽以全身而退的旁观者身份跟随剧情发展,肯定或否定角色的行为,但在故事内容的接受之外,其所实现的是对个体心灵的追问与思索,即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意义上的“净化”。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讲述其在北京研究生毕业后,毅然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投身扶贫一线的故事。黄文秀毕业回乡扶贫的选择和同乡毕业留在大都市工作形成鲜明对照,让观众在被精英意识和利己主义的裹挟中看到了另一种实现自我的可能。在乡村工作中,观众既看到黄文秀白天摸排贫困户情况的忙碌,又在黄文秀夜里的辗转难眠中感受到扶贫工作的艰辛困苦。而她在夜里写下的驻村日记,不仅是对自己工作生活的反思,更以坚毅的信仰叩问着屏幕前观众的内心。
再者,从内容出发,当下追寻崇高之美的电视剧创作往往以革命历史或时代印记为书写主体,虽然革命事件业已完成并被历史性地记录在册,但如前所述,先烈或民众们上下求索的超越性精神和深沉的爱国情怀,仍能跨越时间洪流召唤当下观众的共通情感——成为崇高美学共时性生成的精神性链接。系列电视剧(也可称“单元剧”)《理想照耀中国》《功勋》等涉及多人物的书写,前者将人物故事划分为“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复兴时期”四大阶段,以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火炬贯穿其中,使看似庞杂的40组人物的发展有迹可循;后者则以8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新时代楷模为书写对象,展现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在不同领域和岗位为国奉献的责任担当。崇高精神的贯穿不仅是单元式电视剧架构的线索,也是历史或时代人物与当下观众跨时空对话且共鸣的桥梁。
同时,由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印痕,观众也在此过程中由个体被询唤为主体。但此种“询唤”所完成的不仅是观众对于家国历史的深刻认同,更是唤醒了人类对超越性力量和崇高之美的集体认同。当下的观众生活在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分裂的工业社会中,“一方面由于经验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原本是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内在的崇高精神被琐碎的庸常和分裂的现实所遮蔽,闪烁的光辉和纯洁的心灵在现代性的异化中消失不见,大众在机械性的生存中把自身依附于分裂的残片中,失去了寻回崇高性的能力。但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与工业机器的部件,他们是有情感爱恨的能动主体。因此,电视剧作为生活化的一面镜子,不仅铭刻着历史与时代的印痕,书写着崇高的本质精神,更是在一次次“询唤”中弥合人民大众因现代性异化而与个体本质产生的裂隙,让他们重新发现自身崇高的力量,也使作为人类本质精神之一的崇高实现了跨越时空与媒介的链接。
结语
崇高是先哲的理性思辨,是艺术创作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本质心灵。崇高是多义的,它可以是宏伟的自然景观,是惊悚的内心震颤,是庞大的物质体量,是高度的技术发展。但它也是纯粹的,它是人类上下求索的精神超越,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是平凡中寻求不凡的砥砺前行,是人类在宏大壮观的形象与事物面前肯定自身的伟大。
崇高美学在新时代电视剧中体现为对人民精神生活的深度关切和积极引领。它要求电视剧在追求市场效益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坚守艺术底线,用优秀的作品回馈观众,用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电视剧通过塑造具有崇高精神的角色,讲述充满崇高力量的故事,引发观众共鸣,激发观众思考,继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因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电视剧创作应该更加注重对崇高美学的挖掘和表达,将崇高的精神追求与大众的文化需求相结合,创作出更多既有艺术价值又有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新时代电视剧创作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在回溯历史和映照当下的过程中发现崇高之美,并以之唤醒人民大众内心潜藏的崇高追求。这既是对大众的精神抚慰与引领,也是对创作市场乱象的整饬与反拨,更是对人类文明与精神高度的思索与探寻。这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电视剧这一艺术形式本身的期待。如此,电视剧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贡献更大的力量。
*本文系2023年中国文联文艺理论研究重点课题“新时代文艺崇高审美价值取向研究”(课题编号:ZGWLBJKT202307)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黄钟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3期(总第114期)
责任编辑:陶璐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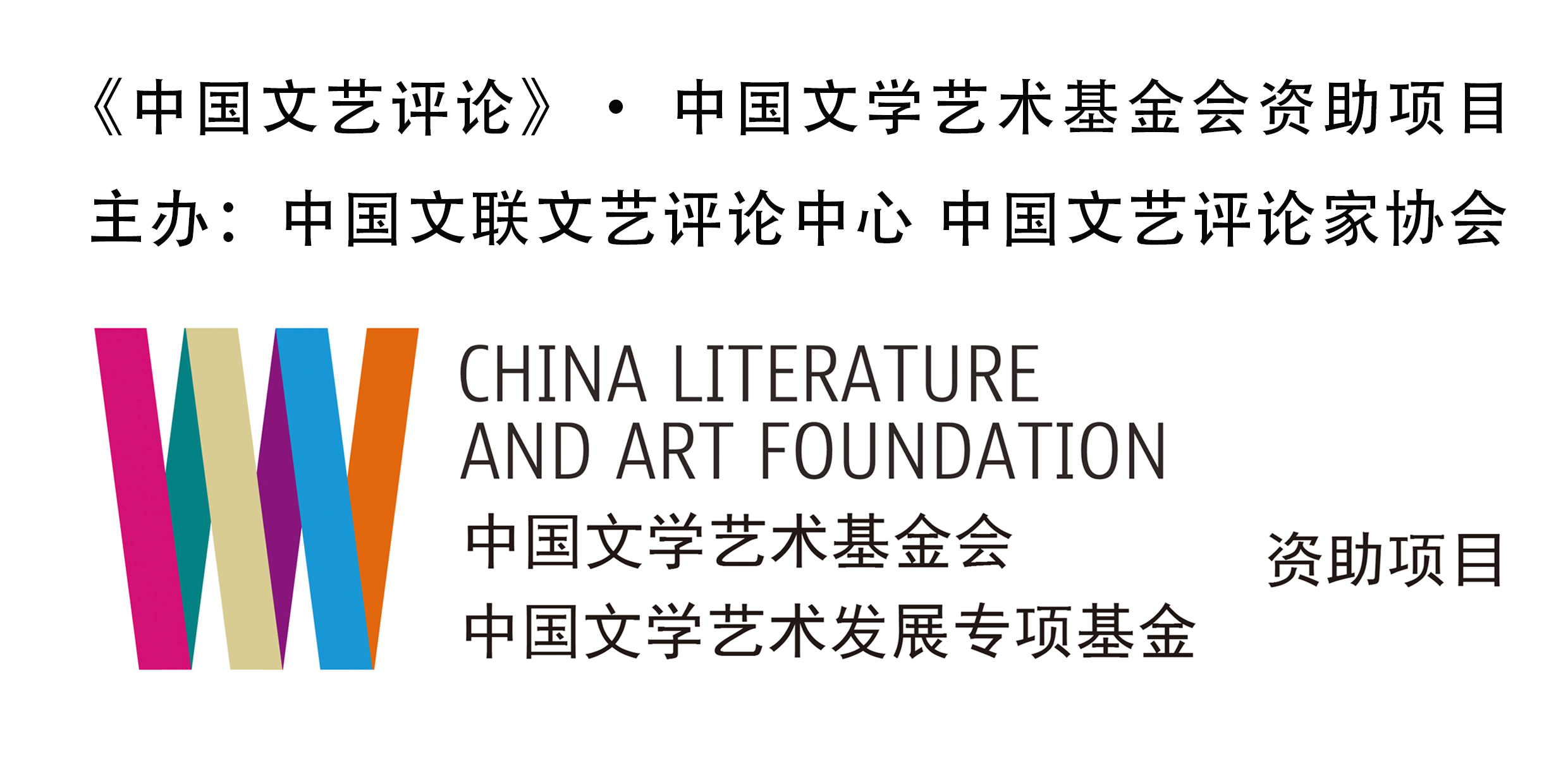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